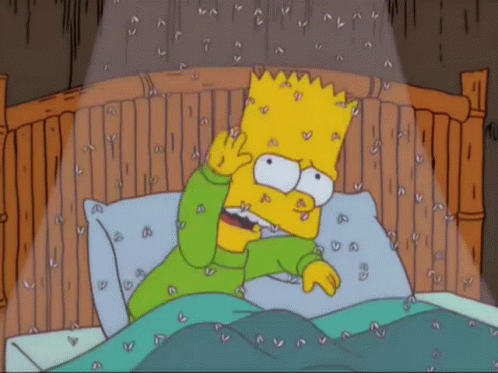為了方便統治,江戶幕府禁止人民隨意遷徙,但出外去「進香」是可以的(宗教面前,政治也得禮讓三分)。因此,除了官方「大名參勤」的大規模移動外,到了江戶後期,經濟較寬裕的老百姓也開始走在旅行的路上。
旅途的風景召喚著畫家的熱情,「名所繪」也應運而生。其中最有名的作品,非葛飾北齋的《富嶽三十六景:神奈川沖浪裏》莫屬。波浪像虎爪,凶猛地讓人移不開視線,北齋巧妙使用當時新進口的普魯士藍染料,創造漂亮的漸層暈染,使這幅畫幾乎成為浮世繪的代名詞。
這次《三十六景》四十六幅畫作中有七幅來台展出,造訪當日再次見到其中四幅,有種遇見老朋友的熟悉和欣喜。但最「殘酷」的展場安排,莫過於將師徒二人的《日本橋》同場陳列。
喔、我真是太喜歡師傅大膽地將人群置於畫面下方(而且還只出現頭頂),作為擁擠但佔比極低的小塊前景,與上方大片留白天空相呼應。